更新时间:2025 07 10 22:34:34 作者 :庆美网 围观 : 22次
大家好,如果您还对阜阳颖州公墓价格表查询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阜阳颖州公墓价格表查询的知识,包括阜阳汝阴候墓之谜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阜阳20多米高的大土堆,就相当于一座小山,可以登高望远。在明朝时期阜阳城建造的奎星楼,仅9米多高,就能望见大别山之余脉霍山,称望霍楼。然而,在今天的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处,四十多年前却有一座20多米高的大土堆。可以遥想当年,那该是多么一座壮观的土山呀!
四十多年前的这座土山位于原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生产队。这座土山当地人称双古堆,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出现抑或是人工垒起,这些已成为历史之谜。所有的一切都静静地卧在阜阳广袤的大地上。1957年,阜阳建飞机场取土对它进行了开挖,从20多米高的大土堆变成了仅仅4米高的土堆。1977年,罗庄大队罗庄建砖窑厂把其全部挖平。然而,就是这一次挖土,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大土堆下面却隐藏着一个惊天之谜:地下竟然埋葬着2000多年前的汉代开国功臣汝阴侯之子夏侯灶,这个大土堆就是几千年来踪影难觅的汉初陵墓,同时也是在阜阳流传几千年的一对仙鸟之谜,梦幻般张扬着神秘色彩的大土堆竟是汉初陵墓发祥之地!
说起汝阴侯及后裔墓葬之地,几十年前人们只会想到陕西西安,谁也没有想到会葬在阜阳。感谢1977年罗庄大队那次建砖瓦窑厂,从地下挖出了两个灰质陶马头。考古工作者闻讯而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随着挖掘的步步进行,一件件文物呈现于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惊呼走进了梦想中的天堂!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竹简和极其丰富的陪葬物品,尽情展示着汉初曾经的富足和风韵。其中仅二十八宿圆盘就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是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失传的《甘石星经》。阜阳出土的大批汉简笑傲全国,主要就是靠这批汉简《诗经》,后来称为《阜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它展示了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最重要、最有价值、可读性最强的惟一一部经书的早期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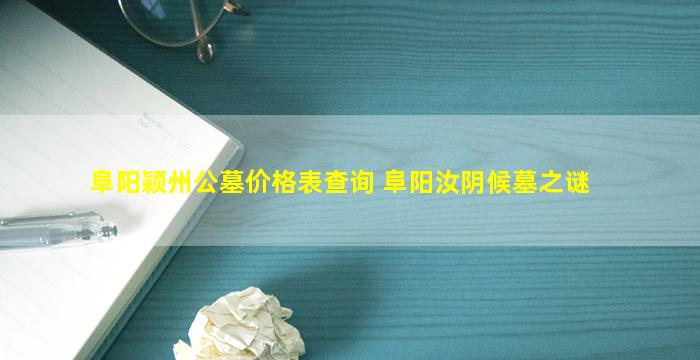
“好像就是在这里,当年有个飞机场跑道,挖掘的墓葬在飞机场跑道左侧,附近还有一个大深沟。但这些都没有了,我在北京呆了11年,回来又十多年了,变化这么大,真确定不了是不是这里”。站在阜阳师范学院新建的大楼后面,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指点着眼前近一米高荒草,表情显得有些疑虑。他说,既没有当年的飞机场跑道,也没有罗庄生产队居住的房屋,真不好判断。在这一片空白而开阔的场地没有任何参照物,我实在搞不清楚他指点的具体方位。但我知道,韩自强的目光已经穿透了27年前那次挖掘现场,在寻找当年墓葬之地到底在哪里?
2004年10月13日,韩自强陪同我们一行驱车前往双古堆。作为参与当年文物考古发掘者之一的韩自强,已有二十多年没有来过此地。他致力于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研究,已出版两部书。可以这样说,对于汝阴侯墓研究他是最有发言权。然而,由于时光久远的缘故,他已记不清当年汝阴侯墓确切的地点。在阜阳师范学院西侧一正在施工的工地上,看到了一群正在干活的建筑工人。韩自强说,这里干活的可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问问他们也许知道。我走上前去询问,当年这里一座双古堆在哪里?几个干活的工人指着一个人对我说,你问他就行了,他可是当年亲自挖掘过双古堆。这位叫李会启的工人,今年已62岁。他说,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还找墓干什么。我说,想看一眼当年所在地,同时也想感受一下千年前的气息。他对我说的话有点不太明白,不过,他没再问。用手指着阜阳师范学院这座高校,就是这座高校正前面一二十米处。随后,他带领着我们来到了当年汝阴侯墓葬所在地。指着校门前我们脚下踩的大理石地面说,就是这里了。我有点感觉不可思议,真不敢相信这里就是当年的双古堆汝阴侯墓葬。见我疑惑,李会启说,阜阳师范学院建这座楼时,曾把线划在汝阴侯墓葬上面,村子里人都纷纷议论,说这大楼要把墓建在下面,可是非常不吉利。后来,这消息传到师范学院领导层,再后来就把楼向后退了几十米。对于他讲的教学楼向后退了几十米,韩自强分析认为,学校领导不可能迷信而把划好线的地基向后退。可能是因为汝阴候是座大坑,地基松软,不利于建高楼,所以向后退了,在建筑工程中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李会启对我说,那位戴眼睛的是不是博物馆的人。我点点头。李会启说,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他,当时他还很年轻,在现场负责文物挖掘。很快,韩自强认出了他,是当年罗庄大队抽四个人帮助清理古墓的人之一。李会启说,当年他才35岁,罗庄生产队抽出四个人帮助挖土舀墓里的水,每天给10个工分。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叙话时,都感觉到双方老了。是的,27年前的汝阴侯古墓挖掘,两个人都很年轻,一个负责文物考古的青年,一个是队里出工分干活的青年。光阴荏苒,日月如棱。转瞬间,两人再回首,已都是60岁的人了。
李会启还回忆小时候的双古堆,那时候双古堆没有什么像样树木,仅有不多的杂树,不太高,小时候他们经常与伙伴跑到双古堆顶上玩耍,玩抓敌人捉特务,还玩滑滑梯,从大土堆上直接滑下来,有时衣服划破了回家告诉父母在别处玩碰破的,都不告诉父母是在双古堆玩划破的,因为父母不让小孩子到双古堆玩。可能当时双古堆过于冷寂神秘,同时,那还是一处坟场地。与李会启一同干活,在五里庙居住的谢风良回忆当年双古堆情景时说,当年的双古堆跟现在师范学院的8层楼差不多高,方圆占地大约有十几亩地。小时候在家里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双古堆,他们经常跑到双古堆玩耍,当年双古堆周围都是一片光秃秃,没有树木,有一些说不上名的矮小杂草类,双古堆附近全部是白土。大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阜阳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霜将麦子打冻了。双古堆附近居住的村民听信谣言,用双古堆上的白土能够救活小麦,于是大家纷纷到双古堆拉土挑土施到麦地里。直到阜阳建飞机场垫跑道,挖双古堆的土垫,一下子把双古堆挖的还有四五米高。
今天的双古堆因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早已走进了历史。双古堆的墓中文物早已得到了妥善的抢救性发掘,我们在庆幸27年前那次紧急抢救性发掘中得到的许多宝贵文物同时,心中也或多或少地对当年贡献惊世文物的双古堆产生了怀念。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前的双古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从双古堆汉墓发掘中又如何判断是西汉汝阴侯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夫妇之墓的呢?
今年已80高龄,从市党史办离休多年的王襄天老人,他当年曾作为文物工作者参与汝阴侯墓挖掘,给我提供了一份当年《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文件》。文件内容是《关于双古堆西汉墓发掘情况的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大致可以了解到当年双古堆是怎样的情形。双古堆位于阜阳市西南角,紧靠飞机场的西侧。据当地群众反映,它原是两个紧相连的高大土堆,故得名“双古堆”。双古堆原高出地面二十余米,东西长一百米,因1957年修建飞机场时从上面取土垫跑道,所以现仅有四米多高。据《正德颍州志》记载:“城西南五里有双冢湖。”经调查双古堆周围确是洼地。近年来,罗庄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已平整土岗和大小土堆七十多个。1977年春,罗庄大队又在双古堆建立了砖窑厂,计划把双古堆挖平。窑厂在取土做砖坯时发现有出土的古代陶马头,经派人鉴定和对双古堆钻探调查研究,确认双古堆是年代较早的夯筑土坑古墓,并立即向地革委和省文化局、省文物队作了汇报。随后,又和阜阳县、社、大队初步商定结合罗庄大队平整土地对该墓进行发掘。4月12日地区展览馆将上述意见书面报省文化局。后经省文物队派人进一步钻探,认为墓确有挖掘价值。因当时正值抗旱紧张,所以推迟到7月1日才动工。上面一段是我从当年的内部文件中了解到的。由此我们可知当年双古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了。
当年亲自参与墓葬发掘和文物整理工作的韩自强和王襄天两位老人回忆:1977年7月1日至8月8日发掘了双古堆西汉墓两座。经过对古墓的发掘,发现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双古堆两座汉墓的漆器和铜器上有“女阴侯”铭文,西墓中又出土了“女阴家丞”封泥,漆器铭文有“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年数,这些都为判定墓主人及其年代提供了确切的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女阴,故胡国”。属汝南郡,故城即今阜阳。女阴侯是汉高帝刘邦对其功臣夏侯婴的封号。夏侯婴与刘邦同为江苏省沛县人,参加了刘邦的起义军后,多次立功。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为汝阴侯,在朝中任太仆,一直到吕后当政。吕后死后,他以太仆的身份参与了废少帝立代王为文帝的斗争,死于汉文帝八年。夏侯婴的儿子夏侯灶,汉文帝九年嗣位,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夏侯婴孙子夏侯赐,于汉文帝十六年嗣位,死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在位三十一年。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于汉武帝元光二年嗣位,于汉武帝元鼎二年畏罪自杀,在位十九年。汉武帝除去了汝阴侯的封号,食邑也被取消了。汝阴侯共四代,凡历时八十六年。汉宣帝元康四年,虽曾诏令夏侯婴的玄孙之子长安大夫信复其家,但再没有恢复汝阴侯的称号了。
那么,汝阴侯墓出土了多少文物呢?我们从当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物局三个单位关于双古堆发掘简报中,来了解一下当年出土文物的数量及相关情形。这两座墓葬内死者的尸骨都无残留,内含有漆皮和碎陶片,由于早期被盗,随葬器物全被扰乱,有的器物因棺椁塌毁砸压破碎,完整的已不多。残存的器物都放置在头箱和边箱内,棺床上除了铜镜、带钩外,别无他物。在东墓头箱西南角单扇门内横放着一把漆鞘铁剑,剑刃虽锈,但还锋利。剑的北边放置银扣长方漆奁、耳杯、长元盘、唾器、小陶罐等。洗去漆盘上的污泥,看到底部刻的铭文,考古工作者兴奋异常。铭文是:“女阴侯布平盘,径尺三寸,七年吏讳工速造”。这件平盘的发现,是墓主人自报家门。从而让考古工作者知道了这座墓是汝阴侯家族墓。在靠近南椁壁陈放着大小银扣漆盘、银扣三足漆卮、漆匜、杯、壶、桃形银镶片、铜镜、弓弭、漆勺、弦枘、陶编钟、陶编磬、铜弩机、铜斗(勺)、银削柄、不知名漆器、半两钱、骨、牙雕碎件以及木俑、木兽座、马饰件等。东边箱和头箱的头部有许多彩绘漆片,是木笥残片。许多器物原放在木笥内,因木笥破坏而散乱。放置的物品有铁剑、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栻盘架、铁锤、石磨、太乙九宫占盘、漆布奁、木弓、铜镞、铁杆箭、铜生肖印、铜带钩、金泡钉、错金银铜轴头、铜环、竹简。东边箱东北角有铁甲胄,卷放在一个木笥内(只有木笥残片)。西边箱陈放有鎏金铜弦枘、木杆、铜行灯、子弹形铜器、金箔盾饰、铜戈、铅网坠、漆脯奁等等。棺床框架上塌下的木炭内有一鎏金铜牌,西北角椁盖板上有一件铜矛,北边箱还放有铅弹丸等。东墓出土文物最多,共有206件文物。西墓内放着一件髹漆彩绘鸠形木质仪仗。棺床前陈放有铜镜、漆盘、耳杯、盂、卮、奁、陶盒等。东边箱放置有陶马头、鼎、盒、壶等陶器,均已残破。西边箱有陶盒、银鐏和三块“女阴家丞”封泥。还有残破的竹篾编织物,似竹笥,笥内装有葫芦子、麻子、鹿角、猪趾骨等,在棺床东北角棺盖板下还有两面小铜镜,此次西墓出土文物共有64件文物。此次发掘汝阴侯墓共两座,共累计文物272件。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2000多年,年代太久远,当我们再次凝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已无法准确描绘当时的真实情景,只能从古文献中去寻寻觅觅。
双古堆在历经2000多年的时光后,除了沉积出惊世的汉简及天文仪器外,还给世人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东西。具有历史性价值的文物达270件,而其中的汉简和三件天文仪器尤为珍贵,也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遐想空间。今天,尽管缔造这些文物的古人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但我们仍然可以穿越历史,寻找古人留下的历史遗存,去领略古人遗留的占卜、天文和文化风情的魅力。阜阳汉简北上1977年从双古堆出土的大量汉简,因早年墓被盗塌陷,汉简、漆、泥土混合在漆器里,不仅散乱扭曲,变黑弯曲,而且全部黏连在一起,成为类似刨花板样的朽木块,已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这些扭曲不被人注意的汉简当时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同时混在泥土中的三件罕见的天文仪器又是如何命名的呢?
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为把这批汉简剥开在北京一呆就是整整十年,韩自强在北京与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又是如何把这些黏结在一起的汉简剥开并把文字整理出来的呢?如今已过去了27年,作为现在研究双古堆出土文物的考古专家韩自强,他在这27年里整理出多少篇有价值的阜阳汉简呢?当年参与文物考古发掘的王襄天老人回忆,1977年7月1日开始发掘至8月8日结束,历时38天,汉简是在第36天才被发现的。就在考古发掘进行到最后两天时,8月6日,安徽省考古专家殷涤非同志来到汝阴侯墓挖掘现场。他在观看挖掘出来的文物时,发现了许多粘结在一起的漆片,好奇的他就拿起一块木笥(漆的竹片),用刷子刷几下,没想到,木笥被刷子刷过后,出现了一行行小字。殷涤非仔细辩认,发现是一行带“疒”字偏旁的字。在一旁的王襄天激动地大喊起来,竹简!竹简!发现了漆片上有字,随后,考古文物工作者迅速把散落在墓地旁的全部漆片收集起来,带回到了阜阳地区博物馆。与此同时,在这批残破的漆器中,其中还有三件比较罕见的珍贵文物。一个是刻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圆盘,圆盘是木胎髹漆的,分上下两盘,大小如同盛菜的瓷盘。另两个是方形漆盘,都是上下两层,犹如方形带盖的石砚,揭开看,上面也都刻着星宿和图象。当时王襄天和韩自强他们认为是天文仪方面的东西。初步给那个带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圆盘定名“二十八宿圆盘”。对另外两件因不懂其用途就没有命名。阜阳汉简及三件天文仪器的出土,不仅引起了当地文物工作者的惊喜与关注,还引起了省、国家考古专家的关注。因为汉简已严重变形扭曲、腐朽粘结,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三件天文仪是漆器,它一离开水就要干瘪变形。如何识别、保管已成了当时阜阳地区博物馆的头疼问题。为此,省博物馆要求迅速带到省里进行保护和研究。
1977年9月23日,王襄天和韩自强把这文物全部用棉花层层包住,里面再撒上大量的水,从阜阳乘飞机带到合肥。然而,送到省文物工作队,省考古专家吃惊地发现,在安徽省还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根本搞不懂如何保护,曾想做“扒皮”处理,但担心会把仪器上的字搞掉了。针对这种情况,省考古专家给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打电话请求支援。北京方面的考古专家因没有见到实物,不知道汉简变形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天文仪器,也就无从谈文物如何保护的问题,只告诉他们带往北京进行研究和保护。9月30日,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再次带着这批珍贵文物乘飞机前往北京。到达后,被指令送到“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一生研究漆器的保护专家胡继高接待了他们两人,从湿布包里打开这些文物,连胡继高也惊讶有如此多的汉简,看到天文仪,胡继高认为可以完整地保护下来,但汉简破损严重,已薄如纸张,互相叠压镶嵌、粘结变形,给剥离揭取工作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经过判断胡继高认为须泡在药水里剥离开,并要求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留下来当助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胡继高用药水泡并剥离是十分正确的。罕见的天文仪器刚到北京那几天,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为了弄清带来的这三件天文仪用途和姓名,他们两人又去考古研究所找夏鼐所长。当时夏所长正忙着去伊朗讲学的准备,没有见到。便找科技史专家王天木、自然博物馆专家薄树人、席泽宗,因这几位专家要一起参加美国天文学家座谈会,一时不能在一起研究。后又去请教古文字学家唐兰和天文学家顾铁符、考古学家张政琅、严敦杰等专家。他们对这三件天文仪器,都赞叹不已。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听说阜阳的汉简和天文仪器带来了,便抽空看了文物,又和古天文学史专家薄树人、席泽宗、张政琅、严敦杰等专家对这三件天文仪定了名。对带有二十八宿的那个圆盘,同意王襄天和韩自强他们定的“二十八宿圆盘”。对那个有圆形天盘和方形地盘并刻有冬至、夏至等天文用语的一件,取名“太乙九宫占盘”;对刻有北斗星图象的天盘和刻有二十八宿地盘的一件,定名为“六壬栻盘”。困扰阜阳考古专家的这三件天文仪终于初步知道了是什么仪器之名,但因资料失传,其使用方法和作用还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研究。那么,时隔27年后的今天,这三件天文仪器初步研究应该有些眉目了,它对于对于我们了解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而这三件天文仪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韩自强说,当时在双古堆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这三件罕见的栻盘形制用途各异,为我国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现。在中国古代,天文与占卜是分不开的,“栻”既是测天文以定时日的工具,又是占卜用具。古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占卜,而占卜与天文是分不开的。《史记·龟策列传》中,春秋时宋元公召博士卫平圆梦,卫平就曾扶着栻盘定日月星辰的方位为之部析。王莽最信占卜,当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城火焚宫殿时,他还叫天文郎把栻盘放在他面前,按当天的时辰星象方位,顺着栻盘上北斗星的斗柄指向而坐度祈祷(见《汉书·王莽传》)。王莽时的“六壬栻盘”,1972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了一件,其形制和汝阴侯墓“六壬栻盘”大同小异。现在国内外所藏出土或传世的另外几件栻盘是东汉和隋代的,它们没有这次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栻盘年代早,而且只有六壬栻盘一种。那么,这三件栻盘是不是古代人测天而用或别的用途呢?韩自强因这27年一直致力于阜阳汉简的研究对这三件天文仪器作更深的研究。让我们从1978年第八期《文物》上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中寻找这三件罕见的天文仪器风貌。
二十八宿圆盘,为上、下两盘,皆呈圆形。上盘直径23.6cm,边厚0.4cm,下盘直径25.6cm,边厚0.5cm,两盘中心有圆孔相通。上盘面刻6颗圆点,与盘心圆孔正好连成北斗星座图象。过圆心划有一轻痕十字线,边缘排一周小圆孔,孔如谷米大,不透穿,因边缘稍破,小圆孔总数经推算为365个。下盘刻二十八宿星名和各宿距度。二十八宿圆盘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特别是下盘所刻的二十八宿名称和各宿距度,根据唐《开元占经》所辑,是战国时代《甘石星经》中的名称和数据。《甘石星经》已经失传,但是它的数据保留在二十八宿圆盘上,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六壬栻盘,分天盘、地盘。天盘在上,为圆形,直径9.5cm,厚0.15cm;地盘在下,成正方形,边长13.5cm,厚1.3cm。天盘中间刻北斗七星星座,边缘刻十二月次和二十八宿。地盘中间放天盘处稍突起,地盘边至天盘间刻二道方框线,框内有3层文字:外层是二十八宿,每边7宿;中层是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等),每边3个;内层是天干(甲、乙、丙、丁等),每边2个,并把戊、己刻在四角。在内层的四角分别刻有“天豦己”、“士斗戊”、“人日己”、“鬼月戊”。这个盘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既有占天之用,又有其医学上的实用价值。
太乙九宫占盘,分上、下两盘,上面的上圆盘放在下面方盘的凹槽里。小圆盘直径8.3cm,厚0.3cm,方盘边长14.2cm,两盘中心有圆孔可以通连。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金木水火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上刻划的九宫数字排列则与后世的“洛书图”完全符合。而“君、相、百姓”等又都是《灵枢经·九宫八风篇》中的内容。《灵枢经》是《黄帝内经》(中医学书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成书年代约在战国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天气的变化与人体的关系,以占风候,治疾病。这个盘的刻划实为《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的图解,其用途与天文、医学有关密切的联系。过去曾有人怀疑《灵枢经》是唐人的伪托之作。太乙九宫占盘的出土,证明了这种说法不正确,为《灵枢经》成书于秦汉之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韩自强的10年时光可以说,提阜阳的汉简,就离不开韩自强。今年68岁的韩自强,从事文物考古生涯已达42年。回忆当年阜阳汉简进京并在北京呆的10年,韩自强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1977年10月25日,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从北京坐火车回到阜阳。组织安排王襄天回到阜阳县文化局,并负责筹备四九起义革命文物陈列馆。韩自强则被借调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阜阳汉简和整理和研究工作,谁知,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时光。韩自强在北京整理汉简,每天都是一个人自己做饭洗衣。提起在北京呆的10年,韩自强仅用一个“苦”字来形容。1980年春节过后,韩自强便来到北京。汉简经过药水浸泡后,还须经过更多繁琐的工作,才能揭开粘结的汉简,而揭时还须提防别掉了字。韩自强每天一上班就点燃炉子,把汉简放在锅里蒸,蒸了几个月,觉得太慢,便改用消毒纱布包起来放在锅里煮,煮透以后再用刀片一层层剥离揭开。每一块汉简都像普通纸一样薄,揭开一条用玻璃片夹住,然后逐个编上号,再用照相机拍照留资料。仅这项简单操作工作就干了两年多时间。随后又用了三年时间记录简上的文字,再一一分类找出处。这项工作量最大,因为每片汉简上只有一句话或几个字,甚至有时仅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半个字。还须按照古籍查找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出处,碰到残缺不全的字,简直无法查找。随后的几年,把这些清理过有文字的汉简用蒸馏水浸在密封的玻璃管里,共装了2000多管100多盒进行保存。经过十年的整理,阜阳汉简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批汉简原长约25cm,宽1cm多,用三道绳子编联在一起。除少量的木简、木牍之外,大多为竹简。阜阳汉简实乃历代文献书籍,有竹简、木简和木牍,但其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目前已清理识别出《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和木牍等十一种古籍。
OK,关于阜阳颖州公墓价格表查询和阜阳汝阴候墓之谜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嘿,各位球迷们!你们准备好迎接卡塔尔世界杯了吗?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世界杯的情况如何吧!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卡塔尔世界杯的历史背景。作为第一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备受关注的卡塔尔世界杯。随着比赛的进行,四强球队的预测也成为了热门话题。那么,哪些球队最有可能闯入卡塔尔世界杯四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让我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即将到来的卡塔尔世界杯四强球队!相信很多球迷们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究竟有哪些球队能够跻身这场备受瞩目的赛事的前四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
大家好,最近卡塔尔世界杯的各项奖项公布了,球迷们都在热议谁将获得最佳球员、最佳青年球员等奖项。那么在历史上,世界杯最佳球员和最佳青年球员是谁呢?卡塔尔世界杯的评选标准又
大家好!随着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临近,相信各位球迷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场盛事的信息了吧?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篇全面的生活百科,让你轻松掌握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历
卡塔尔世界杯,这场备受瞩目的足球盛宴即将在不久的将来拉开帷幕。作为足球迷,你一定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场比赛的信息。但是你知道吗?除了比赛时间安排,卡塔尔世界杯还有许多令人


